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科幻电影越来越受欢迎。如今,人们拥有先进的造梦技术,可以通过图片将想象力丰富的人梦中的世界完美还原到他人眼中。然而,科幻电影的魅力远不止想象力迸发的壮丽画面。那些富含人类对未来和未知世界的哲学思考,显然更加神奇。
最近一部名为《湮灭》的科幻电影大受欢迎,它的设定背景是人类探索一个被“闪光”笼罩的未知区域。人们在未知的旅程中发生了什么?对于人类来说,突变是湮灭的结束,还是永生的开始,值得思考。
2014年,美国作家杰夫范德米尔的科幻小说《遗落的南境》击败刘的《三体》,以——星云奖获得当年的科幻奥斯卡奖。很多中国读者在感叹《三体》的同时,也对这部惊悚、隐晦、明显的魁苏鲁风格小说《谭》感到惊叹。所以,当《遗落的南境》的第一部三部曲《湮灭》被改编成电影后,自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然而有趣的是,导演本人甚至连原著都没看就坦率地开始改编剧本,以至于最终呈现在大银幕上的作品情节和人物与小说大相径庭,几乎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103010讨论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当意想不到的变化来临时,我们该如何面对?“变”的概念一直是科学幻想的核心,电影将其提炼为“折射”“分裂”“湮灭”三个角度。
电影《湮灭》海报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1、从光的折射到基因突变
“折射”是最适合屏幕表现的视觉现象。影片刚开始不久,当镜头第一次投射到“X区域”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片被五颜六色的肥皂泡包裹的森林。从牛顿的棱镜实验开始,人类就知道在看似纯白的太阳光中,存在着不同的单色光。当它在不同的介质中传播时,由于各种单色光的偏转角度不同,彩虹就会出现。影片中的“肥皂泡”暗示光线在这个区域折射。当探险队的五名女科学家进入该地区时,所有的无线电通讯设备都失灵了。对此,物理学家乔西(故事中的人物)解释说,无线电波和光波一样,会在区域内部发生折射,因此无法正常接收。
但这个科幻故事试图讨论的显然不仅仅是光线通过水杯时日常可见的物理折射:它将这一概念扩展到了基因层面。我们知道,基因是一条带有核苷酸序列的多肽链。大多数时候,基因靠自我复制生存。然而,有时基因可能会在复制过程中发生变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基因突变。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那么如何理解故事中虚构的基因折射呢?我们可以把基因自我复制的过程想象成一束光沿着一个方向移动。当这个过程发生折射,不同物种的基因相互交融,于是我们在电影中见证了长着鲨鱼牙的鳄鱼和头上长着树枝的梅花鹿。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奇异而妖娆的美。
在这个“x区”,人只是众多被整合的物种之一。当探险者在途中看到同一株植物上开着不同的花时,有人问:“这是一种疾病吗?”生物学家莉娜回答说:“从人类的角度来看,是的。”影片中,当这位物理学家全身长满藤蔓,融合成大片绿色植物时,脸上的表情几乎是自由的。而那个身体沿着泳池壁长成奇怪“壁画”的士兵,也被镜头刻意展现出一种奇怪的美感。作为人类,他们已经消失了,在改变后留下了另一种形式,但生命终究被延长了。问题是,我们能接受吗?
2、从分裂到永恒
“分裂”也是故事中反复出现的核心意象。导演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细胞分裂的生物过程与“永恒”联系在一起。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影片开头,生物学家莉娜在课堂上给学生们展示了一张细胞分裂——的图片,这是一个癌细胞,是从一位美国黑人女性HenriettaLacks身上提取的,因此得名“海拉细胞”。癌细胞和正常细胞的本质区别在于,正常细胞会经历一个衰变的过程,但癌细胞可以无限增殖。作为一个人,哈丽特拉克斯于1951年去世。作为一种生命形式,海拉细胞从离开人体到现在已经“活”了67年。它遍布世界各地的实验室,广泛应用于癌症研究、生物实验或细胞培养等科学研究。它的总质量已经超过5000万吨,在可预见的未来它还将继续存在。
当一个细胞被分成两部分时,它的形状非常类似于数学符号“”,意思是“无限”。这个符号在电影中反复出现。起初,在X区的河上划船时,莉娜的手臂上开始有莫名的淤青。当她最终逃脱时,左臂上的纹身清晰可见。除了莉娜之外,同为旅人的安雅和前探险队的士兵们的手臂上也有“”符号。
事实上,这种模式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大毒蛇”。柏拉图形容它是宇宙的祖先,嘴里叼着尾巴,象征着永恒的轮回。这个符号更多的时候是以一个简单的圆圈出现,在电影刻意将其扭曲成“”之后,象征意义就凸显出来了。
p>衔尾蛇 资料图片
我们此时必须接受,生命的变化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发生。那么现在影片抛出了“永生”作为诱饵,代价则是自我身份的彻底消解。此时的问题又回到了“变化”本身:当这种变化导向“永生”的时候,是人类可以接受的吗?
3、湮灭的隐喻
此时,我们终于遇见了故事的第三个层次:湮灭。
影片中心理学家文崔斯博士说:“自杀和自毁是不一样的,自毁是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湮灭与毁灭也是如此,毁灭意味着消亡和结局,而湮灭指向的则是物理意义上的变化过程。具体来说,物理学中的“湮灭”,指的是物质与其所对应的反物质在接触之后,物质消失、能量释放的过程。它的后果并非两种事物共同消失于虚无,而是由物质转化成了能量。在影片中,这种变化成了一种有力的隐喻。
在影片中,进入灯塔直面外星生命的人类一共有3个,按时间顺序分别是女主角的丈夫、得了癌症的心理学家以及女主角本人。影片中的外星生命并无形体,那个最初浑身银色的人形生物不过是外星生命与人类接触之后发生的变化。这个变化便是“湮灭”:“身体和思想都将被分解成最小块,直到无一剩余”。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论是外星生命还是人类,作为旧的生命存在形式都将死去。在此之后,新的生命便从中诞生,它不但重新塑造肉体,也将延续记忆。
细胞分裂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在影片中这一过程并未发生在心理学家身上——永生的癌细胞打破了死亡的进程,湮灭的变化无法完成;女主角的丈夫在自我认知崩溃之后选择了自我毁灭,活着出去的那个新的生物尽管延续了他的面容和记忆,但也仅仅是在灯塔和其中的外星生命真正毁灭之后,才成为完整的个体;至于女主角本人,她的记忆时断时续,又在显微镜里两次目睹了自己细胞的改变,经历了一切之后,手臂上的文身清晰可见,眼睛也与她的“丈夫”一样发出怪异的闪光——湮灭已经发生,她既不是人类,也不是外星人。
于是我们又一次回到了那个终极的问题。“人”这一生命形态,以及“我”的自我认知,都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种变化是可以接受的吗?
4、克苏鲁与现代文明的恐惧
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其实创作者本身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应,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变化”已经在进行当中,无论我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
我们早已意识到,现今人类的躯体与完美的生物形态还去之甚远。诸如腹中的盲肠、眼中的盲点、扭曲的脊柱、分块的腹肌、外露的耳廓与鼻窦、与食道相邻的呼吸道,甚至是衰老和死亡本身,无一不是物种演化过程当中逐渐在人类身体上积累而成的种种“bug”——更可怕的是,基因工程的发展和生物技术演进似乎彰显了“纠正”这些错误的可能。从古至今,人类所追求的“永生”也许就在前方向我们招手了,我们是否真的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
此时我们遭遇了与《湮灭》中的人类相类似的困境。从器官的补正、更换,到基因的筛选、调整,甚至电子芯片的置入,人类的肉体界限早已被无数次打破。无论手臂上是否会浮现出文身作为标识,“我们”已然成为“新人”,或者叫作“后人类”。
人类科技飞驰向前的残影甚至模糊了关于“人”本身的定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后人类”日渐成为一个学术研究界炙手可热的课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要到哪里去?这些穷尽了人类几千年的智慧也无法得到解答的问题,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里,也许又会有新的答案。
在科学飞速进步的年代里,有许多智者往往是通过书写科技所可能带来的灾难,以此来表现对这一知识系统的强烈忧虑。而对美国科幻、恐怖、奇幻作家洛夫克拉夫特来说,他更加深切地怀疑人类理性本身的有限性。这位作家生活在科学大厦被“两朵乌云”倾覆的年代,牛顿范式当中和谐、稳固、有序的世界图景,正在转向爱因斯坦和量子论范式下,一般人类无法以其直观知性理解的纷杂局面。
这就是“克苏鲁”文学文化所着力塑造的“恐怖宇宙”:“这个世界最仁慈的地方,莫过于人类思维无法融会贯通它的全部内容。我们生活在一个名为无知的平静小岛上,被无穷无尽的黑色海洋包围”。克苏鲁神话不仅仅是书写种种哥斯拉式的庞大怪兽,而是强调它们的形体和生存方式就与我们对“生物”的理解截然二致。例如,其中的“星之彩”的本体是无定形的能量场,通过吞噬生物和陨石在太空中飞行;克苏鲁的海底城市有着非欧几何的造型;而“地球生命之源”大体上就是一大块原生物质。
正如我们现代人类的生活早已凭借种种工具超越肉体的限制一样,克苏鲁神话中怪物们的行为也并不受限于他们的肉身——实际上大多数作品当中,他们往往是以传说、遗迹和心理感应的形式出现。这种强调氛围营造和人类探索行动的特征,使得克苏鲁在近年来日渐成为许多影视和其他艺术形式所乐于采用的题材和风格。
具体来说,这些作品都隐约暗示着一个极其庞大幽远的世界背景,人类以及我们所习惯的日常生活方式,仅仅是其中微不足道的边缘部分。其中的非人生物往往是强大的“巨大开发者_运维问答沉默之物”,对我们人类的存在毫无兴趣也并不在意。故事往往发生在人类试图去追寻和理解这些生物的过程当中,死亡和新生随处可见,但最大的恐怖,则在于对我们习惯经验的彻底颠覆。
克苏鲁神话本质上是对当代科学发展的人本隐喻:我们并不知晓下一个科学发现将把我们带往何方,但对它的磅礴力量却有明晰的触感。洛夫克拉夫特在二战之初就已经去世,而他创作的影响仍在不断扩大。尤其在后来原子弹、基因技术和网络科技的发展面前,这种来自宇宙和历史更深处的未知存在成为一种愈发珍贵的体验。
这种体验是非认知性的。当我们面对量子论或高维空间的困惑时,我们即便无法想象双缝干涉实验的内部机理、四维物体在三维世界中的投影过程,但至少还有数学作为描述和解释的工具。而克苏鲁神话抗拒提供理解这些非人之物的可靠路径,在他们面前,“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那种高扬的人文精神,反而被晕染上了夜郎自大的意味。人类真正能做的事情,是在彰显自己的好奇心与认知冲动的同时,保持谨慎,随时准备接纳全新的历史走向。
链接
克苏鲁风格
克苏鲁出自美国小说家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克苏鲁的召唤》,书中对克苏鲁作了正面的、详尽的描绘。克苏鲁是象征“水”的存在之一,形象为章鱼头、人身,背上有蝙蝠翅膀的巨人。克苏鲁是神话中的一个邪恶存在,是旧日支配者之一,是克苏鲁神话的形象代表。
在小说中,克苏鲁是从外星球飞来地球的邪神。由于星位错误(或旧神所为),他被封印在太平洋中南部深海中的拉莱耶古城中,处于假死状态,无法活动。但是,他绝不是真正的死亡,他会不断做梦——海水屏蔽了这种精神波动。世界上那些具有艺术天赋、精神敏感的人或神经异常者常常能感觉到这种波动,从而在他们的梦中出现克苏鲁和利耶城的形象,最终导致重病、昏迷乃至发疯。
所有克苏鲁神话的相关作品都不曾对克苏鲁的神力做过具体的描述。因为克苏鲁多半处在被封印的状态,有些时候可以透过心电感应与外界沟通。克苏鲁会通过这些感应让人做噩梦,或者产生强迫思考,强烈暗示等作用。有些时候克苏鲁还会透过心灵传授的形式传授他人法术或者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知识,但是因为他与人类的精神层次相去甚远,有些时候与他接触的人类会变成痴呆或发狂。克苏鲁主要的信仰者叫深潜者。
新怪谭
美国编剧、作家杰夫·范德米尔夫妇本世界初曾编辑出版过一本厚厚的集子叫《新怪谭》,这种集纳本身就是对“新怪谭”一词进行阐述。范德米尔这样形容“新怪谭”:一种以都市为舞台、架空世界的小说,它颠覆了传统奇幻中常见的概念演绎,以真实复杂的现实世界为起点,创造出兼有科幻与奇幻元素的文学设定。“新怪谭”可以被称为一个阶段,一次文学运动,它的特征被新作者用来当作原料,与其他元素相混合,再次制造出新奇而精彩的变化。
新怪谭的诞生主要来源于两个方向。一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科幻新浪潮运动,以M·约翰·哈里森、迈克尔·莫考克等人为代表,大举施行实验性写作,并刻意模糊科幻与奇幻的边界。杰克·万斯的《濒死地球》即是此类“科学奇幻”的代表。另一个源头则是洛夫克拉夫特之后发展起来的新恐怖小说。在洛夫克拉夫特时代,恐怖故事的焦点就是“恐惧”,而其中怪物的秘密从来没有得到揭示或解释。但后来的恐怖小说则将重点放在描写畸形怪兽本身,详细地展示出怪兽的每一个细节。新怪谭继承了这一特征,将具体化的怪物作为故事的核心,从而超越单纯的“恐惧”,赋予其更丰富的内涵。
米耶维的巴斯拉格三部曲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新怪谭作品,以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伦敦为模板,创造出一座假想的城市,并涵盖了欧洲城市近代以来的各种政治纠结。同时,巴斯拉格世界中也有许多奇特的类人种族,包括鹰人、虫首人、蛙人、仙人掌族等。这套书的出版是新怪谭真正在商业上的成功,也鲜明地表现出米耶维式风格。由于其交织的奇幻、科幻、荒诞等多类元素以及令人咋舌的细节描写和浓郁的政治色彩,巴斯拉格三部曲被评论界称为新怪谭的范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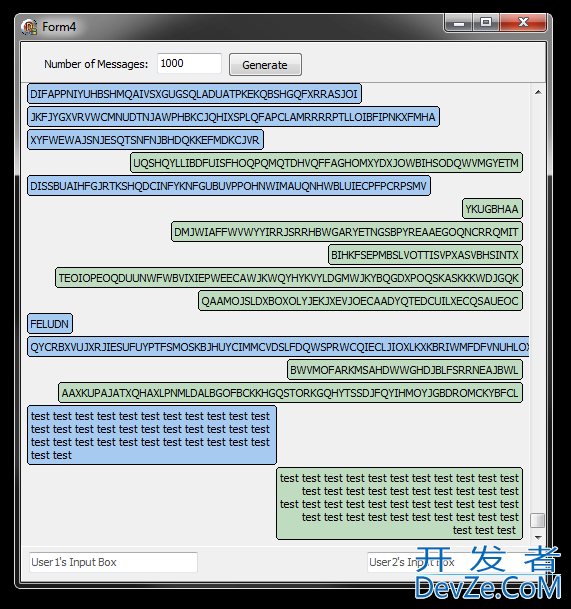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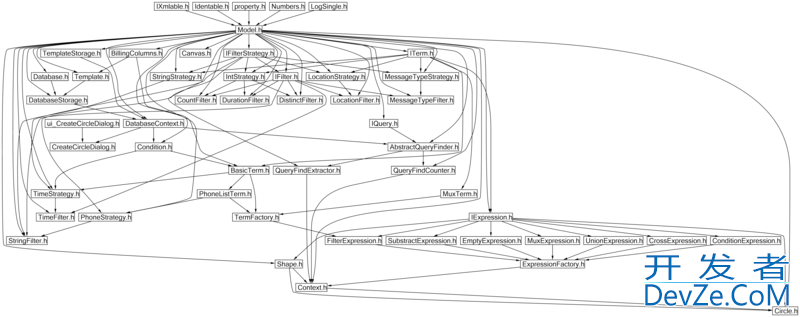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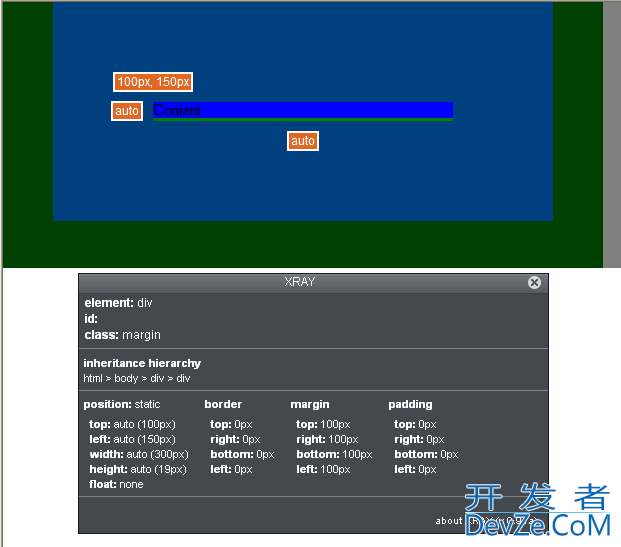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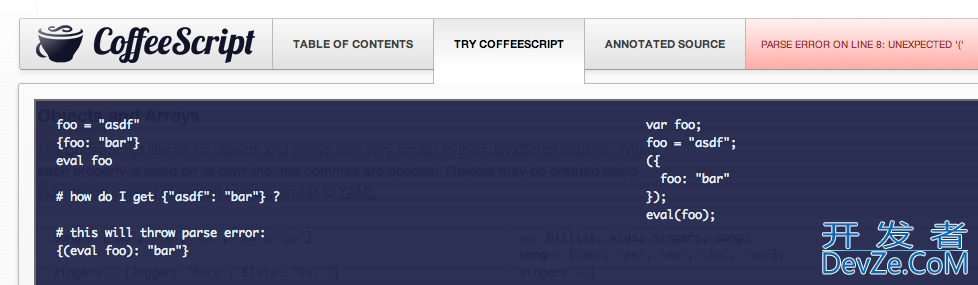
![Interactive visualization of a graph in python [closed]](https://www.devze.com/res/2023/04-10/09/92d32fe8c0d22fb96bd6f6e8b7d1f457.gi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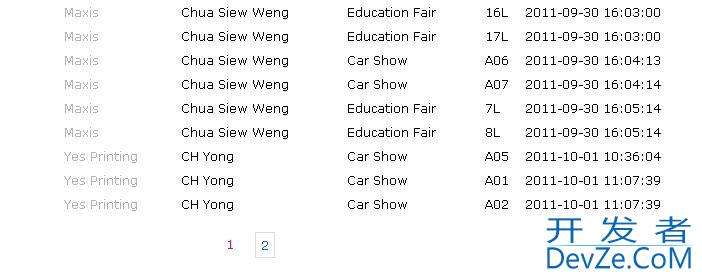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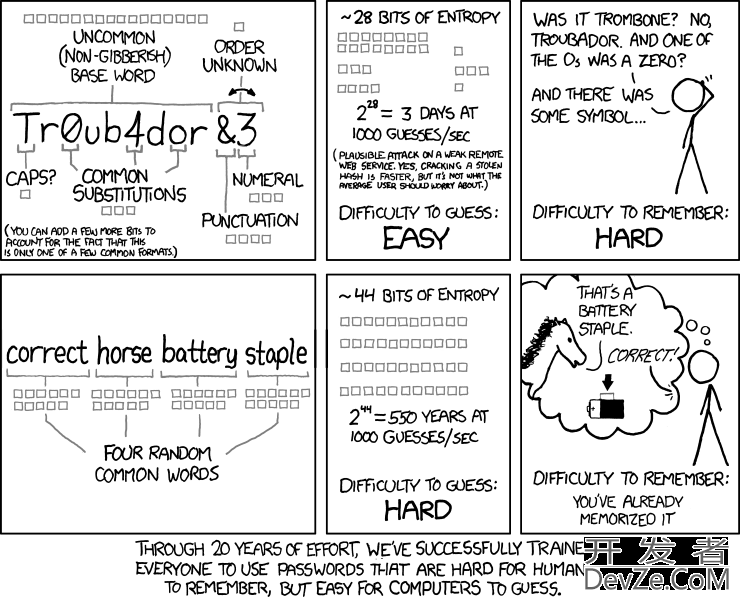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